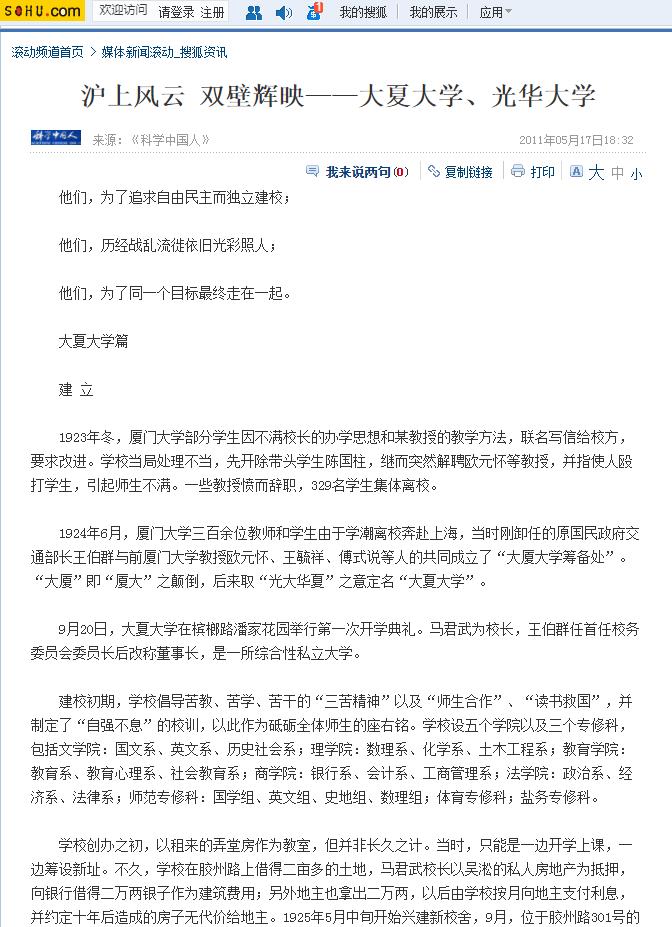他们,为了追求自由民主而独立建校;
他们,历经战乱流徙依旧光彩照人;
他们,为了同一个目标最终走在一起。
大夏大学篇
建 立
1923年冬,厦门大学部分学生因不满校长的办学思想和某教授的教学方法,联名写信给校方,要求改进。学校当局处理不当,先开除带头学生陈国柱,继而突然解聘欧元怀等教授,并指使人殴打学生,引起师生不满。一些教授愤而辞职,329名学生集体离校。
1924年6月,厦门大学三百余位教师和学生由于学潮离校奔赴上海,当时刚卸任的原国民政府交通部长王伯群与前厦门大学教授欧元怀、王毓祥、傅式说等人的共同成立了“大厦大学筹备处”。“大厦”即“厦大”之颠倒,后来取“光大华夏”之意定名“大夏大学”。
9月20日,大夏大学在槟榔路潘家花园举行第一次开学典礼。马君武为校长,王伯群任首任校务委员会委员长后改称董事长,是一所综合性私立大学。
建校初期,学校倡导苦教、苦学、苦干的“三苦精神”以及“师生合作”、“读书救国”,并制定了“自强不息”的校训,以此作为砥砺全体师生的座右铭。学校设五个学院以及三个专修科,包括文学院:国文系、英文系、历史社会系;理学院:数理系、化学系、土木工程系;教育学院:教育系、教育心理系、社会教育系;商学院:银行系、会计系、工商管理系;法学院:政治系、经济系、法律系;师范专修科:国学组、英文组、史地组、数理组;体育专修科;盐务专修科。
学校创办之初,以租来的弄堂房作为教室,但并非长久之计。当时,只能是一边开学上课,一边筹设新址。不久,学校在胶州路上借得二亩多的土地,马君武校长以吴淞的私人房地产为抵押,向银行借得二万两银子作为建筑费用;另外地主也拿出二万两,以后由学校按月向地主支付利息,并约定十年后造成的房子无代价给地主。1925年5月中旬开始兴建新校舍,9月,位于胶州路301号的新校舍落成,学校随即全部迁入。
但形势的发展,让原来计划行不通了。一方面,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在学生中更掀起爱国热潮,同时也遭遇了军阀以及外国军队的镇压,处于租借的校舍已经很不安全了。另一方面,随着学校声誉提高,大夏学生人数激增,1928年秋季学期时学生人数已达千人以上,胶州路校舍已无法承载。1927年初,马君武应邀去筹建广西大学,辞去大夏校长职务,王伯群先生任校长,决定择地建立永久性校舍。
从1929年3月起,大夏陆续在沪西梵王渡中山路旁购地近三百亩(现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北路校址)。当年夏天,由前校长马君武、欧元怀、王毓祥先生率领几位华侨同学去南洋一带募集建设新校舍的经费。王伯群校长则以六万七千余两银子(合当时11万余元)资助建筑教学大楼,并以中山路地产为抵押,向银行借贷建筑费32万元。
1930年初,中山路校舍开始动工,同年9月一期建筑完工,包括:教学大楼“群贤堂”,可供2000人同时上课;“群策斋”、“群力斋”两栋男生宿舍以及女生宿舍“群英斋”,3栋宿舍各可容700人;此外,还有教职员宿舍12幢,以及学生浴室、饭厅等。于是,大夏大学随即迁入,将胶州路校舍交给大夏附中使用。接着,在新校址上又继续兴建理科实验室、体育馆、医疗室、大礼堂、东西大楼教职员宿舍以及各类运动场,至1932年大体完工,此外,在学校西南部,另有四百亩土地,辟为大夏新村,为教职员自建住宅之用(抗日战争前已建成30余所);还有荣宗敬捐赠丽娃栗妲河婉蜒秀丽,更为校园增添了美景。在当时上海40多所私立大学中,大夏大学尤以建筑宏伟、环境优美、设施较完备而著称。
西南三迁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上海“八一三”事变后,大夏被迫内迁。最初与同为私立大学的复旦大学合并成为联合大学,一设庐山,称复旦大夏第一联合大学,一设贵阳,称第二联合大学。庐山联大以原复旦师生为主,贵阳联大则以原大夏师生为主。
不久,日军进犯江西,复旦再迁重庆北碚,大夏迁到贵阳,两校之间的联合解体。在贵阳的大夏大学,最初假当地讲武堂上课,嗣后打算兴建校舍,1939年贵州省政府曾拨贵阳花溪公地,加上当地人士的捐赠,共有一千亩左右。1940年8月,新校舍开工建筑,但因经费不足,只完成校舍三栋。需要一提的是,1942年2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拟将大夏大学与贵州农工学院合并,改名为国立贵州大学,引起大夏师生强烈抗议,遂奔走各方与各校董商议,要求教育部收回成命,终得维持大夏大学仍得保存原名与维持其私立性质。
1944年冬,日军进犯黔南,大夏三迁赤水。王伯群校长因迁校劳累成疾,于同年12月逝世于重庆。孙科在重庆召开校董会,推选贵州省教育厅长欧元怀为校长,王毓祥为副校长。1945年3月,大夏师生和公物到达赤水,赤水地方人士与教育界同仁热情赞助,立即让出文昌宫大庙给大夏作校本部,还有贵州省立赤水中学、私立博文中学、县立女子中学都分别借给大夏一部分校舍,首先安置好教室、图书馆、职工宿舍、办公室和厨房、饭厅、学生宿舍,在短短一个月内便正式上课。
重返上海
大夏内迁之后,仍留沪上的吴浩然和1938年由贵阳派回上海的鲁继曾、邵家麟等先生,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上借得重华新村房舍,设立大夏大学沪校,使无法转往内地的一些学生得以继续学业。
1945年8月10日,日本投降,大夏师生同赤水民众欢欣鼓舞,举行提灯火炬游行,欢庆胜利。1946年9月,大夏师生及公物安然回到上海,直至1949年始终保持私立大学性质并保留校名至1951年。
抗战初期,上海大夏中山路校舍毁于炮火者甚多,幸群贤堂、群策斋等尚存。抗战胜利后加以修缮整理,1946年春季学期,沪校即开始在此上课;秋季学期时,在贵州的大夏师生也陆续回沪。之后,学校曾重建大礼堂“思群堂”与女生宿舍“群英斋”,并在群力斋废址上建造平房数排名为“新力斋”,在教职员宿舍区造了几排平房。还计划另造新图书馆,已购置了不少建筑材料,因国民党政府通货膨胀,货币贬值而没有造成。
解放以后,在大夏大学中山北路校址上建立华东师大时,由大夏移交给华东师大的校舍,共计建筑面积17606平米。
大夏是一所私立大学,其经费来源只能是学生缴纳的学费,这就决定了学校的经济状况不可能很宽裕,特别是创办之初,应当说是相当窘困的,所以很难以高薪去聘请教授,一些名教授之所以愿来大夏授课,在相当程度上是看到大夏那种兢兢业业、自强不息的办学精神。
大夏首任校长马君武(1880—1940)是我国第一个在国外获得工学博士的化学家,又长期帮助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其声望之高可以想见。1924年11月,他出任大夏大学校长,并亲自讲授化学课程,就完全是尽义务的,他从未要学校支付薪金或车马费,而且为了建筑胶州路301号的校舍,还把自己在吴淞路的房地产作抵押向银行贷款。1929年夏,他已离开大夏,还带领欧元怀等去南洋募捐以帮助大夏建筑中山路校舍,这种精神,堪称楷模。
第二任校长王伯群(1885—1944)虽然也曾留学日本并进过研究院,但因长期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所以不以学术见长,但最初作为大夏的董事长,也主张大夏应“本学术研究之自由与独立,涵育革命与民主精神”。1927年继马君武任大夏校长之后,就始终认为校长最主要的责职,就在于为学生选聘优质教师。在他任校长期间,把这些精神贯彻始终,为大夏具有较好的师资条件而不懈努力。
大夏的第三任也是最后一任校长欧元怀(1893-1978)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修习教育学科并为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所赏识的中国留学生之一,他深刻认识师资力量对一所学校具有极其重要,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性的意义。他作为大夏的创始人,毕生为大夏物色优良的教师不遗余力。
在这些校长的主持下,历年来大夏聘请了大批学识渊博的知名教授为学生授课:
物理学家夏元生是爱因斯坦的学生,也是在中国最早介绍相对论,他曾任北京大学理科学长,1924年来大夏大学任物理学教授,1938—1944年任贵阳大夏大学教务长兼理学院院长,并亲自为学生讲授普通物理学、光学、电学、热学、电子论、相对论、量子力学、波动力学、理论物理、近代物理、解析几何、高等微积分、群论、科学通论等课程,直至1944年8月18日在大夏任教时逝世,可以说是为大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王伯群校长对夏教授逝世感到悲痛欲绝,当时的国民政府也曾明令褒扬夏元教授,大夏大学还曾为夏元教授发起遗属养育金运动,建立夏元授奖学金等。
社会学家吴泽霖先生,1928年初从美国留学归国不久,他的母校清华大学与大夏大学同时向他发出聘请。论条件,当时的大夏大学还在艰苦创业之中,无法与早已是名校的清华大学相比,但大夏师生朝气蓬勃、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却使他深为感动,因而宁愿选择在大夏。不久,燕京大学又以相当可观的待遇为条件,两次邀聘吴先生,吴先生以“我应当帮助大夏”作答。在大夏期间,他不仅为学生讲授社会学方面的课程,还组织学生进行社会调查,并先后发表了许多社会学的论著、译著和教材。抗战军兴,他随同大夏师生内迁,曾任复旦、大夏第一联合大学的教务长,继而又至贵州任贵阳大夏大学的教务长、文学院院长、历史社会系系主任和社会研究部主任。在此期间,他组织学生深入贵州少数民族地区,调查民族分布、民族习俗和民族关系,将调查所得材料写成民族学的论著,还为大夏建立起“民族文物陈列室”。吴泽霖先生也成了举世闻名的民族学者,至1941年,他才离开大夏至西南联大任教。
儿童教育专家沈百英先生与其他许多教授不同,沈先生既未出国留学,甚至还没有读过大学,只是一名中等师范学校的毕业生。但杜威先生曾听他一课,对他的教学评价甚高,由此风闻全国。在他担任尚公小学校长期间,大夏大学教育系的同学前去参观,大家对他十分钦佩,欧元怀校长得知之后,即不拘沈先生的学历,邀请他来大夏为教育系学生讲授《小学教材教法》。沈先生上课总是以他自己的切身体会教育大家要热爱儿童教育事业,然后以生动而具体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讲授在教学中怎样循循善诱使儿童饶有兴味地学习各种知识。此后,沈先生又在光华、沪江等大学任教,成为上海的名牌教授。1951年后,他继续在华东师大任教,直到他以90高龄退休。 其他硕学名师举不胜举,只能从略。
以上仅是几例,其实大夏大学教授更是囊括了马君武、何昌寿、邵力子、郭沫若、田汉、何炳松、李石岑、朱经农、程湘帆等。不仅如此,校董更有孙科、吴稚晖、叶楚伧、邵力子、张嘉森、傅式说、王志莘等,甚至炙手可热的杜月笙也曾屡次资助大夏,可见大夏当时的盛况。
学生培养
大夏大学建校27年,培养学生近20,000名,毕业生6,000余人。包括一批为国为民的有识之士,如熊映楚,曾是武汉农民运动的重要干部;雷荣璞、陈国柱分别是广西、福建建党干部之一;吴良斌(亮平),最早翻译恩格斯《反杜林论》,解放后曾任中共中央党校顾问;郭大力、周扬、叶公琦、陈赓仪等都在大夏大学学习。学校培养了一批杰出的专家学者,如胡和生、陈子元、李瑞麟、刘思职等四位中科院院士,翻译家戈宝权,儿童文学家陈伯吹,古典文学评论家王元化和青铜器专家马承源等,还有不少杰出的政治家、企业家和其他知识界人士。
香港血脉
40年代末,江山易帜,大夏大学部分教员及学生南下香港,在香港复校,定名光夏书院。1956年6月,光夏、平正、华侨、广侨及文化五所书院合并成立“联合书院”,定址香港坚道147号。1963年,联合书院加盟香港中文大学。
光华大学篇
“六三”事件
1925年5月,上海日本纱厂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等,激起上海各界人民群众的极大愤慨,纷纷集会抗议,遭到帝国主义分子的血腥镇压,酿成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中国人民纷起反抗,掀起了大规模的爱国反帝运动。
就在英国巡捕在五卅血洗南京路那天的黄昏,有个原圣约翰肄业并曾目击惨案真相的交通大学的学生聂光樨奔至圣约翰大学报告这一事件,全校的空气顿时震荡。当晚学生们就集会商议,决定第二天早晨不按惯例取学校教堂做早祷,而是去思颜堂开会,并约好也是圣公会办的几所中学的同学前来参加。6月2日再次开会,决定于6月3日在大学图书馆前升起中国国旗。三十多年来,圣约翰大学的旗杆上一直飘扬着美国国旗,而这次却升起中国国旗,显示了久被压抑的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在苏醒。
然而未隔多久,同学们发现国旗被校长卜舫济夺去,经推代表交涉无效,于是向童子军团借了一面,仍悬半旗,为五卅惨遭屠杀的烈士志哀。一时掌声雷动。卜舫济闻声出现,勃然大怒,蛮不讲理,将旗掷地,践踏于脚下。当场宣布:学校从当天起放暑假,全体学生必须立即离校!同学们压不住心头的怒火,附中同学杨子英睹此情况,放声大哭,愤慨地说:国旗横遭凌辱,是可忍孰不可忍!
广大师生非常气愤,大学及附属中学学生553人以及全体华籍教师19人,集体宣誓脱离圣约翰大学,10余名应届大学毕业生声明不接受圣约翰大学颁发的毕业文凭。他们还提出收复教育权、创办中国人自己新学校的豪迈口号。
建 立
离校师生的反帝爱国行动,得到了学生家长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学生王华照之父王丰镐(字省三)先生,慷慨将祖坟地90余亩捐做校址;学生许体纲之父许沅(字秋朋)先生捐开办费5000元;沪海道尹张寿镛(字泳霓)先生也是学生家长,除个人捐款3000元外,他还发行“建筑公债”20万元资助办学;朱经农先生自告奋勇承担向各方募捐经费的任务。
经过短期的努力,新校很快就建立了校董会,由王丰镐仔董事长,聘请张寿镛为校长,朱经农为教务长,学校定名为“光华大学”。辛亥革命以后社会上传诵着古代的一首《卿云歌》,其中有两句歌词是:“日月光华,旦复旦兮”,马相伯先生办的复旦大学即取名于此。光华大学寓“光我中华”之意,象征着复兴中华,反抗帝国主义割宰和奴役的革命精神。光华以日月卿云为校旗,红白为校色,“格致诚正”四字为校训,6月3日为学校成立纪念日。
9月,光华大学成立,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路)租房上课。报名入学时,脱离圣约翰大学学生、各地学生亦闻风来校就读,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同时举行,给声明退出圣约翰的应届毕业生颁发毕业文凭,全校学生人数达970余人,大大超出了由圣约翰大学退出的学生人数。从爱国师生退出圣约翰大学至光华大学成立开学,历时只三个月,学校创建速度之快,世所罕见。
发展
诞生于反帝爱国运动的光华大学创办后,得到各方爱国人士鼎力相助,办学条件日益完善。1926年1月,学校在王丰镐先生所赠大西路地内建筑正式校舍。当年9月,新校舍基本建成,大学部和中学部先后迁入上课。经过十余年的建设,至抗日战争前夕,校园面积已达百余亩,建成教室2幢,学生宿舍3幢,教职员宿舍2幢,以及礼堂、图书馆,科学馆、体育馆、实验室、小工场等。
建校初期,学校设文、理、工、商四科14个系,其中文科包括:哲学、西洋文学、政治、教育、历史、国文、社会;理科包括:数理、化学、生物;商科包括:经济、工商管理、会计、银行;工科不设系。另有附中一所。
1929年,学校经教育部批准立案,改文、理、商三科为文、理、商三个学院,工科停办。文学院设国文系(内分国学组、国史组)、英文系(内分文学组、西史组),政治社会系(内分政治组、社会组)、教育系(内分教育组,哲学心理组);理学院设数学系,化学系、生物学系,商学院设经济系,工商管理系、会计系、银行系。张东荪,潘光旦、容启兆,王造时、张歆海、蒋维乔曾任文学院长,颜任光、容启兆曾任理学院长,金其眉,薛迪靖、谢霖、沈章甫、岑德彰曾任商学院长,各院系教授亦多为国内知名人士。在校学生最多时曾达1700余人,其中大学800余人,高初中900余人。至1938年,毕业大学生1118人,高中生1026人,初中生509人,共计毕业2653人。
1932年,以教育系同学为主,创办光华大学实验中学(1933年立案时改称光实中学)和光华大学实验小学(后改称光实小学)。文科和附中的学生还利用课余时间举办光华义务小学和平民夜校,为附近的农村子弟扫盲,普及文化知识。
学校管教甚严,纪律严明,学风较佳。特别注重国文、外文和数理等基本科目教学,教员上课多用英语,学生毕业服务社会后,颇获好评,学校在社会上有较好声誉,被称为上海六大学之一。学生们在致力于学习的同时,课外活动和体育竞赛也开展得生气勃勃,在江南八大学校的国语、英语演讲比赛中屡居前茅,还曾获江南八大学校网球、足球、越野赛的锦标。
抗日战争
1937年8月13日,日本军队进攻上海,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光华大学大西路校址正好处在两军激战地带,全被日寇焚毁。张校长迫不得已,带领全校迁入公共租界汉口路华商证卷交易所八楼上课,上海沦陷后仍继续坚持办学,未曾间断。
成都分校
为图久安之计,张校长与校董会商定,入川设立分校,加聘谢霖,邓汉祥,甘绩镛、缪秋杰,康宝志为校董,并请商学院院长谢霖担任筹备主任,全权筹备一切。不久,学校租定成都新南门内王家坝街房屋为校址,开始修葺,并由谢霖垫开办费。
1938年3月1日,“光华大学成都分部”在蓉开学,4月6日,补行开学典礼。6月举行“六三节”光华成立纪念时,张寿镛校长赴四川分校并致辞。不久,成都分校新校舍建设也展开了, 1939年初,成都新校落成,全体学生由市内王家坝校址迁到西郊草堂寺迤西,此地改名曰光华村。内中教室两座,“甫澄堂”纪念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赞助,“富铭堂”纪念张富安、仲铭、寿龄昆季之捐校址;学生宿舍两座,“鸣斋”纪念邓汉祥之赞助,“绩斋”甘绩镛之赞助;还有一条道路“绍孚路”,纪念陈绍孚之赞助。同时,此前购买的显微镜天秤等仪器及沪校拨给的图书也运抵四川。建校之初,学校开设政治经济学系,工商管理学系、银行学系,会计学系、化学系,后又添设土木工程专修科及会计专修科,后停办化学系及土木工程专修科。
1945年抗战胜利后,光华大学上海本部立即恢复。由于当时教育部有大学规程不准水久设立分校的规定,决遵张校长寿镛与谢校董霖当初商定成都分部永久留川的计划,决定将光华成都分部移请川省地方人士接办,并将全部校产一律奉赠。根据新校董会议定,新校名称为“私立成华大学”,于1946年2月1日在成都实行交接,王兆荣为成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光华大学成都分部所有校产,经校董会议决赠与川省。
1952年9月,成华大学与西南其他高等院校的财经专业合并,更名为四川财经学院,是建国之初全国高等院校分区布局中的四所财经学院之一,1985年11月更名为西南财经大学。
更名:抗日的另一种形式
1941年以后,由于太平洋日美战争发生,租界亦被日军占领,要求各校向日伪当局登记,张寿镛校长立即表示:“我宁愿解散光华,决不登记。”
为避免日军干涉和汪伪组织的勒令登记,他将上海光华大学名义暂行隐蔽,对外改为两个学社,一名“诚正文学社”,即原文学院,由蒋维乔教授主持;一名“格致理商学社”,原理学院、商学院,由唐庆增教授主持。并经成都分部代呈教育部备案,准许两学社毕业生仍作为光华大学毕业生,给予学位。
抗战胜利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光华大学得以恢复,由于原大西路校址已被日军夷为平地,政府拨给欧阳路旧日侨学校为校址。所不幸的是张寿镛校长未曾享受抗战胜利的喜悦,于日本投降前二十七天在沪病逝。1945年10月,校董会进行改组,由翁文灏任董事长,朱经农任校长,朱公瑾、廖世承任副校长。
光华大学建校26年,为祖国建设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先后入校学生达14000余人,完成大学学业获学位者2400余人。其中有中国社会科学学部委员邓拓,中科院院士徐僖,著名学者周而复、赵家璧、张芝联、吕翼仁、张允和、穆时英、田间、姚依林、乔石、尉健行、荣毅仁、董寅初、黄辛白、柴泽民、黄鼎臣、邵洛羊、杨小佛、谢云晖、杨纪珂、张承宗等一大批著名政治活动家和民主人士。
张寿镛:光华之魂
张寿镛认为强寇压境,只是一时的“艰难”,是“狼突豕奔”,还比较容易“应变”;而如果不注意人才培养,或者培养出来的人不“合辙”,那么他日的艰难将更甚,以致会被人“鲸吞蚕食,其患无穷”。国家富强的根本在于教育,创办光华大学的中心是从帝国主义手中收回教育权。
1930年光华建校五周年,张校长曾写过一篇《光华五周年纪念书序》,其中有一段谈到当时创校之时向富商大贾、达官贵人募捐的艰辛:“方其经营之时,狂奔疾走,呼号相及,借甲偿乙,补屋牵罗,托钵题缘”。那时在上海霞飞路(即今淮海路)、杜美路(即今东湖路)租赁了校舍,并在枫林桥盖了十多间茅舍作为中学的讲堂,“筚路蓝缕,疲于奔走,凛凛焉惧风之飘摇!中学的学生以茅屋为讲堂,寒天暑地,眩涌其中,师若弟宴如也。”张校长写这篇《序》时,已度过困难时期,不仅建立起了大学和中学校舍,还盖起图书馆和体育馆等。
由于光华大学是中国人自己兴办的大学,许多博学之士不计报酬、不图名利,纷纷前往任教出力。张校长还聘请著名的教育行政专家朱继农为大学教务长,廖世承为附中主任,继而延聘到许多国内著名学者教授:廖世承、钱基博、张歆海、韩湘眉、蒋维乔、胡适、徐志摩、李石岑、陶行知、黄炎培、潘光旦、章乃器、王造时、罗隆基、何柄松、钱钟书、叶圣陶、谢霖甫等都曾在光华大学及附中工作过。当时社会舆论认为上海各大学的师资,以光华为首。
担任光华大学校长20载,张校长呕心沥血,把办好光华大学来实现百年树人的理想。他常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当年,在校学生张令杭家境清寒,由张校长资助就读,并嘱其课余校对《四明丛书》,及至大学毕业。
光华大学校训是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张校长在王阳明学说的基础上有所创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贵在实行,不尚空谈”,要“说得出,做得到”。从光华当时开设的专业来看,除政治、社会、教育、文学和历史等系科外,很大一部分是有关发展实业的,包括土木工程、经济、会计,银行、工商管理等。他反对在培养人才上“闭门造车”,以致“车不合辙”。他主张光华毕业的同学应当力求使自己所学的知识能“合辙”,这就是他所说的“知行合一”。
张校长主持正义,对校中进步师生力加保护。1930年,光华政治系教授罗隆基在《新月》杂志上发表文章,主张维护人权,批评国民党专制。当时教育部竟饬令光华大学把罗隆基撤职,为此,张校长上书据理力争。1933年白色恐怖越来越残酷,上海各大学的进步学生80多人被捕,其中有光华大学学生14人,包括诗人田间,作家周而复等。这些学生被捕后,张校长出于对青年学生的爱护,向当时上海特别市市长吴铁城力保他们。
合并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适应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需要,1951年7月17日,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宣布,经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批准,成立华东师范大学。8、9月间,大夏大学的中文、英文、历史、社会、数学、化学、教育、教育心理、社会教育系;光华大学的国文、英文、教育、数理、化学、生物系;同济大学的动物、植物系;复旦大学的教育系;东亚体专的体育系、体育专修科和沪江大学的音乐系相继并入。10月4日,组建了华东师范大学临时工作委员会(后为行政委员会)。10月16日举行开学典礼,正式宣布华东师范大学成立。11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任命华东教育部部长孟宪承兼任校长,孙陶林、廖世承为副校长。
原文: